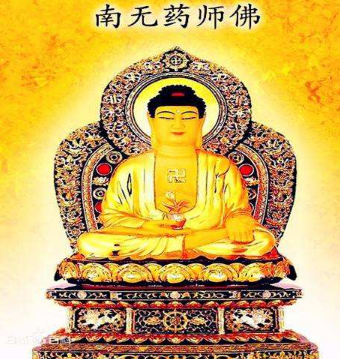一个佛教徒的科学观--学诚法师
发布时间:2019-10-14 10:14:40作者:药师经功德网一个佛教徒的科学观--学诚法师(发帖人:贤萍)
——在2008年10月25日中北大学“科学视野中的佛教”研讨会上的发言
(10月25日 上)

三百年来,科学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果被用来改造自然界,并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并不一定真正懂得科学是什么,由于科学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人们对之产生越来越坚固的信赖,这种信赖也反过来加速了科学的发展。但另外一方面,人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比如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废弃物的过度排放而遭到破坏;由不同人群组成的社会环境,因为资源的争夺和占有而相互仇恨甚至发生战争;乃至于同一个人群中间,因过于看重物质利益上的得失,而发生不和与争执。除此之外还有:人们因为享用现代物质成果而引发的种种疾病,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压力。这些状况都让物质利益短暂满足所带来的幸福大打折扣。

那么,人类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呢?科技的发展增强了人类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这样的努力最终能实现人类的幸福吗?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有过这样的忠告:“单靠知识和技巧,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和高尚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的理由,把那些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的传播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对我来说,人类应该感谢释迦牟尼佛和耶稣那样的人物,远比应该感谢所有创造性的好奇的头脑的成就要多得多。”在爱因斯坦看来,仅仅靠科学技术,还不足以让人类过上幸福的生活,人类还要建立自身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并以此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曾接受过西方最高水平科学教育的马蒂厄?里卡尔后来皈依佛教,完全投身到佛教的实践中,他认为:“外部世界的改造有其极限,而这些外部改造对于我们的内部幸福所起的作用也有其极限。外部条件、物质条件的好转或损坏,固然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幸福,但是最终,我们不是机器,幸福或者不幸的是精神。”(《和尚与哲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23页)既然如此,对精神世界的改造就变成了他生命的主要方向。
在这方面,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做出了表率。他出身于印度的王公贵族,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太子,拥有世间人所希求的一切美好禀赋:崇高的地位、强大的权利、耀眼的名誉以及美丽的妻子。然而太子却认为这一切都是无常,很快都会失去,自己最终也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可怜地死去。别人也一样,都难以逃脱老、病、死等痛苦。想到这些,他便选择放弃王位、离开家人,过着清淡简朴的修行生活,最终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获得了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在此后四十多年的生命里,他一直在为众生分享着他证道的喜悦,并竭尽全力地帮助一切人得到这种喜悦。
佛教认为人类的痛苦源自内在的无明,其主要目的是要消除这种痛苦的根源,而不是在外在境界上做过多的努力,否则非常容易在忙碌中迷失方向,最后变得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痛苦。如《大智度论》说:“问曰:佛自说佛法,不说余经,若药方、星宿、算经、世典,如是等法,若是一切智人,何以不说?以是故,知非一切智人。答曰:虽知一切法,用故说,不用故不说。有人问故说,不问故不说。”(卷第二)《大智度论》说:“于十四难(一、世界及我为常耶?二、世界及我为无常耶?三、世界及我为亦有常亦无常耶?四、世界及我为非有常非无常耶?五、世界及我为有边耶?六、世界及我为无边耶?七、世界及我为亦有边亦无边耶?八、世界及我为非有边非无边耶?九、死后有神去耶?十、死后无神去耶?十一、死后亦有神去亦无神去耶?十二、死后亦非有神去亦非无神去耶?十三、后世是身是神耶?十四、身异神异耶?)不答法中,有常、无常等,观察无碍,不失中道,是法能忍,是为法忍。如一比丘,于此十四难思惟观察,不能通达,心不能忍,持衣钵至佛所,白佛言:‘佛能为我解此十四难,使我意了者,当作弟子。若不能解我,当更求余道。’佛告:‘痴人!汝本共我要誓:若答十四难,汝作我弟子耶?’比丘言:‘不也。’佛言:‘汝痴人!今何以言:若不答我,不作弟子。我为老、病、死人说法济度,此十四难是斗诤法,于法无益,但是戏论,何用问为?若为汝答,汝心不了,至死不解,不能得脱生老病死。譬如有人身被毒箭,亲属呼医,欲为出箭涂药。便言:未可出箭,我先当知汝姓字、亲里、父母、年岁,次欲知箭出在何山、何木、何羽,作箭镞者为是何人、是何等铁,复欲知弓何山木、何虫角,复欲知药是何处生、是何种名,如是等事尽了了知之,然后听汝出箭涂药。’佛问比丘:‘此人可得知此众事然后出箭不?’比丘言:‘不可得知。若待尽知,此则已死。’佛言:‘汝亦如是!为邪见箭,爱毒涂已入汝心。欲拔此箭作我弟子,而不欲出箭,方欲求尽世间常、无常、边、无边等,求之未得,则失慧命,与畜生同死,自投黑暗。’比丘惭愧,深识佛语,即得阿罗汉道。”(卷第十五)
但作为发了大心的菩萨,为了能够利益众生,需要精通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作为接引众生的方便,其中医方明、工巧明都属于现代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如《瑜伽师地论》说:“菩萨何故求闻正法?谓诸菩萨求内明(五乘因果妙理学)时,为正修行法随法行,为广开示利悟于他;若诸菩萨求因明(逻辑论理学)时,……为欲于此真实圣教未净信者,令其净信,已净信者,倍令增广;若诸菩萨求声明(语言、文典学)时,为令信乐典语众生于菩萨身深生敬信,为欲悟入诂训、言音、文句差别于一义中,种种品类殊音随说;若诸菩萨求医明(医学、药学,又称医方明)时,为息众生种种疾病,为欲饶益一切大众;若诸菩萨求诸世间工业智处(工艺、技术、算历学,又称工巧明),为少功力多集珍财,为欲利益诸众生故,为发众生甚希奇想,为以巧智平等分布饶益摄受无量众生。菩萨求此一切五明,为令无上正等菩提大智资粮速得圆满,非不于此一切明处次第修学能得无障一切智智。如是已说一切菩萨正所应求。”(卷第三十八)
佛教重视内在智慧潜修以及慈悲心显发的特质,对于当今时代科学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能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当代思想大师、法兰西院士让-弗朗索瓦?勒维尔认为:“西方在科学方面胜利了,但它没有值得称赞的智慧和道德。”(《和尚与哲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64页)自从公元前五世纪的苏格拉底到公元十七世纪的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西方哲学一直都具有科学与智慧的双重属性。之后的三个世纪之中,哲学的科学功能被移到科学领域,而其智慧功能则转到政治领域。人们寄希望于通过革命建立公正的新社会,以实现对善、正义和幸福的追求。然而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失败和道德失信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在非科学领域的失败。这种失败使人们精神生活面对虚无主义的困境,不知所措,而西方基督教信仰并不能弥补这种缺憾。太虚大师在《中国需耶教与欧美需佛教》一文中提到基督教和科学对西方人的影响时说:“欧美人生活是科学的,信仰是非科学的,……于是就成了一种破裂的不一致的人生。因此,在宗教信仰上,必须丢掉理智;到现实生活上,又必须丢掉信仰;这是欧美现时之苦闷。”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将西方传统中科学与宗教的矛盾称为“欧洲所特有的精神分裂症或分裂人格”。人们期望这种矛盾的状况因为佛教的引入而能有所改善。英国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认为:“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就是佛教传到了西方。”而法国神经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莱拉更进一步地指出:“我们认为,对于亚洲哲学,尤其是对于佛教传统的再发现,乃是西方文化中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的冲击将会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对希腊思想的再发现同等重要。”西方人苦闷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但他们大部分人还有一定的信仰,而对于许多东方人而言,信仰非常缺乏,即便是本土文化对于自身生活的价值,也有重新认识和发掘的必要。否则,面对着日益发展的科技和被刺激的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人们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加幸福,而是变得更加迷茫与失落。
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时代,人类对科学的崇尚甚于其它任何一个领域。在很多人看来,佛教能否被很好地接纳,取决于与科学的兼容性。在近代科学史上,连续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大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让很多人产生这样一种信念: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绝对可靠和非常有效的!而此研究方法也被强行应用到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研究领域。这种做法容或会给其它领域的研究带来一些启发,但如果认为不这样做就是不科学、就不值得信赖的话,这种认识本身是不完全归纳形成的主观判断,无形中已经偏离了科学客观严谨的精神。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意见。”(《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三卷:268页)太虚大师对此也有过善意的提醒:“科学亦有一种执着牢固莫解,则执着此方法为求得真理之唯一方法,而不知法界实际尚非此种科学方法之可通达也。”(《佛学与科学——新时代的对话》,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7页)实际上,对事物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因研究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企图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所有的领域,就好像企图用牛顿物理学来解释和解决一切物理问题一样,有以偏概全的盲目性。佛教是要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其研究的对象涵盖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并以精神世界的研究为主。精神世界不同于物质世界,它无形无色,无法用现代科学仪器明显探测,传统科学研究方法也就力有不足。佛教认为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内在的无明,当这种无明破除以后,痛苦就会自然消失,快乐就会自然生起。这样得来的快乐是一种永恒的快乐,并不特别强调依赖外在的条件。如《大般涅槃经》说:“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净戒中虽不欲生无悔恨心,无悔恨心自然而生。善男子!譬如有人执持明镜,不期见面,面像自现;亦如农夫种之良田,不期生芽而芽自生;亦如然灯,不期灭暗而暗自灭。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坚持净戒,无悔恨心自然而生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恶时名为欢喜,心净持戒名之为乐。”(卷第十七)《大智度论》说:“是乐二种:内乐、涅槃乐。是乐不从五尘(色、声、香、味、触)生,譬如石泉水自中出,不从外来,心乐亦如是。”(卷第八)因此为了究竟离苦得乐,佛教主要并不是要改造外界,而是要破除内在的无明。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有其必然的方法与途径,这就是佛教里面常说的“闻、思、修”与“戒、定、慧”。
佛教与科学有着不同的使命,科学面对的永远是未知的领域,科学家永恒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探索新的现象、发现新的规律;而在佛教里,佛陀已经彻证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并将这些真相在佛经里做了详细的描述。那么要想破除无明,第一步就是要学习和了解佛的这些认知,这就是“闻”。所谓的“闻”,就不是随便看看而已,泛泛而观是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为什么?佛经描述的是佛的境界,也就是觉者的境界,凡夫很难领纳,所以要靠有教有证的善知识来诠释其中的内涵。这个阶段与科学知识的学习不同,对于科学知识的学习,世间也会有很多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人,但对于佛法的学习,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成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自己找几本佛经,随便看看,就以为懂了,实际上可能连佛法的门还没有进入。通过听闻,领纳佛法真实的内涵以后,还要进一步思维所领纳的佛法道理,并在生活中观察。通过思维观察,内心对事实的真相生起确信不移的认识,这就是“思”。这个阶段与科学知识的学习有类似之处,都是要经过一个思辨的过程,所学的知识才能内化为自己的认知。到此还没有结束,还要根据已产生确信的认知进行“修”,也就是利用已内化的认知来改造内在的精神世界。
那么如何“修”、如何改造内在的精神世界呢?那就要依靠“戒、定、慧”。所谓“戒”,就是行为的规范,在生活中,该做的就去做,不该做的就不做。佛教认为,人的身、语行为是人内心世界的反映,反过来也会影响人的内心世界。符合规范的身、语行为可以让人的内心世界变得有规范,明了是非善恶;没有规范的身、语行为会让人的内心世界变得放荡不羁,杂念、妄念纷飞。有了扎实的戒的基础,就可以进一步修习禅定。所谓“定”,就是内心的专注,不受外界的干扰而专注于已发定解的认知上。在这种状态下,再去观察思择,就能产生很强的改造精神世界的力量和功效,从而开启心性的智慧,破除内在的无明,这就是“慧”。一旦智慧显发,一个人所体验的境界便是佛的境界,是觉者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下,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能感受到的就是无尽的喜悦。这就像是一个生了大病的人,经过一番诊断、治疗,而被完全根治以后的感觉:病痛消失了,得到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内在精神世界改造的结果。而利用科学知识改造外在物质世界,只是使人的需要得到暂时的满足,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和便利。这样一个过程,就好像一个病人,通过各种方式让病痛舒缓,但实际上病根还在,因此所得到的舒适和快乐都是很短暂的。如《大智度论》说:“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不能分别,不知名字相,眼识生如弹指顷,意识已生。以是故,五识相应乐根不能满足乐,意识相应乐根能满足乐。”(卷第八)《瑜伽师地论》说:“乐有二种:一、非圣财所生乐;二、圣财所生乐。非圣财所生乐者,谓四种资具为缘得生:一、适悦资具;二、滋长资具;三、清净资具;四住持资具。适悦资具者,谓车乘、衣服、诸庄严具、歌笑舞乐、涂香花鬘、种种上妙珍玩乐具、光明照曜、男女侍卫、种种库藏。滋长资具者,谓无寻思轮石槌打、筑蹋、按摩等事(谓无推求寻思之心,以轮转石槌打、筑蹋其身,令身滋长。此是按摩之法)。清净资具者,谓吉祥草、频螺果、螺贝、满瓮(瓫盛满物,以赠行人)等事(表吉祥相)。住持资具者,谓饮及食。圣财所生乐者,谓七圣财为缘得生。何等为七?一、信;二、戒;三、惭;四、愧;五、闻;六、舍;七、慧。……非圣财所生乐受用之时不可充足,圣财所生乐受用之时究竟充满。又非圣财所生乐有怖畏、有怨对、有灾横、有烧恼,不能断后世大苦;有怖畏者,谓惧当生苦所依处故;有怨对者,谓斗讼、违诤所依处故;有灾横者,谓老、病、死所依处故;有烧恼者,谓由此乐性不真实,如疥癞病(如患疥时闷极生乐,似乐实苦,妄生乐想,世乐亦然;癞为虫钻,妄生乐觉,富贵亦尔),虚妄颠倒所依处故,愁叹、忧苦种种热恼所依处故;不能断后世大苦者,谓贪、瞋等本、随二惑所依处故。圣财所生乐无怖畏、无怨对、无灾横、无烧恼,能断后世大苦,随其所应,与上相违,广说应知。”(卷第五)
佛教对精神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是实事求是、客观严谨的。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尼采说:“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佛教常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没有体会到特定的精神境界而说自己体会到了,在佛教里就属大妄语,是根本大戒。
尽管佛教主要关注的是内在精神世界的改善,但通过对禅定和智慧的熏习,一个人对外在物质世界也会有深刻的认知。对于这一点,越来越多的现代科学研究结果与佛法不谋而合。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的研究表明,时间和空间都是相对的,它们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有关。当观察者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时间间隔将被延长,而物体在运动方向上的长度将收缩。佛教里讲,如果观察者处于深度禅定状态,那么在他的世界里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就被突破了。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说:“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亦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及威力。于一毛端极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剎,十方尘剎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相对论的研究还表明:质量和能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也就是说虚空中巨大无形的能量聚集会产生有形的物质。有了这样的观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佛菩萨的难思神力能变现出种种资具,如《无量寿经》中所讲的:“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量子力学在微观世界的研究更证明物质形成于空,变化坏灭,反复不已。这与佛教《心经》里所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道理有暗合之处。不过,在佛法中色、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停留在生灭的层次上,还有它更深的内涵。
佛教对于世界的诸多深刻认知已被越来越多的科学事实所证明,但这未必能让现代科学的信奉者有足够的理由承许佛教的科学性,因为佛教大量的认知和观念毕竟不是通过现代科学研究的途径所获得的,很多无法用通常的科学实验来验证。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或爱好者,如果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否定通过别的途径发现的现象,这种态度恐怕未必符合科学客观严谨的基本精神。如汤因比说:“从人的知觉感受到的素材(既知事项)的整个内容中进行随意抽取来客观地研究作为观察对象而选择的领域,科学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要限于如下的情况,即要把‘客观性’这个词的含义确定为:‘人们的意见得到交换时,必然是作为同一的东西反映在所有人的理智中的现象和思考。’但若把‘客观性’定义为‘存在自身的如实的正确反映’,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大智度论》说:“不见有二种,不可以不见故,便言无。一者、事实有,以因缘覆故不见,譬如人姓族初及雪山斤两、恒河边沙数,有而不可知。二者、实无,无故不见,譬如第二头、第三手,无因缘覆而不见。”(卷第二)事实上,对于外界事物的认知方法而言,佛教与现代科学有其根本上的不同。这一点太虚大师在《佛法与科学》上有明确的论述:“科学之方法可为佛法之前驱及后施而不能成为佛法之中坚。……以佛法中坚,须我、法二执俱除,始谓之无分别智证入真如。如瞎子忽然眼光迸露,亲见象之全体,一切都豁然开朗,从前种种计度无不消失者然。科学家譬只知改良所藉用之机器,而不能从见之眼上根本改。今根尘、身心等,皆是俱生无明之性,若不谋此根本改良,乃唯对境之是求、执一之是足,将何往而非瞎子撞屋、颠仆难进也哉!”科学这种认知方法的局限性,使它所认知的真理总有一种相对性。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曾发出过既欣喜而又近于无奈的感叹。牛顿在临终前对自己的一生曾做过这样的评价:“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就象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爱因斯坦则说:“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三卷:46页)对于其中的原因,爱因斯坦在后来的《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查》一文中有相关的解释:“科学是这样一种企图,它要把我们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同一种逻辑上贯彻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感觉经验是既定的素材,但是要说明感觉经验的理论却是人造的。它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适应过程的产物:假设性的,永远不会是完全最后定论的,始终要遭到质问和怀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一卷:384页)这也就是说,单纯通过科学认知的途径永远不可能认识到绝对的真理。那么如何才能超越这种限制呢?爱因斯坦特别称赞了一类具有宇宙宗教感情的人,他认为这种宇宙宗教感情已经超越了恐惧宗教和道德宗教的范畴,具备这种宗教感情的人“感觉到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显示出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并进而要求“把宇宙作为单一的有意义的整体来体验”。爱因斯坦认为具有这种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而且“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作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这“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对常规认知的一种超越。在爱因斯坦看来,宇宙宗教感情的开端早已出现在早期的历史发展阶段中,而“佛教所包含的这种成分还要强烈得多”。(《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一卷:280页)
实际上,在佛教的世界观里并没有起主宰作用的拟人化的神或上帝的存在,一切人的行为和自然界的运动都遵循着因果法则。不仅如此,佛教还认为能认知的心与所认知的境只是认知这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而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件事情。这样就把思维世界与自然界、主体与客体当作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来体验和认知。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一个基础是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则是通过感官知觉间接地获得关于这个外在世界或“物理实在”的信息,然后通过思辨的方法来把握它。事实上,对于物体运动接近光速的领域以及微观粒子领域的研究发现,其所描述的对象已经不再具有固定的属性,而是与观察者自身的状态有密切的关联,在这种状况下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并不存在。不同形式的生命状态看待相同对象所具有的不同属性以及所观察对象运动所满足规律的差异性,如天人看水是琉璃,饿鬼看水是脓血,这在佛教的领域里早已是被谈论的话题了。这种差异性更说明了宇宙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认知的主体,很难明确界定被认知的客体。这些都是佛教超越于现代一般科学认知之处。一个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必定会以好奇而又欣喜的态度来看待佛教对宇宙人生不同寻常的认知。如果真能这样,科学发展的脚步将会更加稳健。反过来,佛教徒的理智成分如果不被忽视或者不被情感的成分所压倒,那么他对于科学所取得的进步也同样会报以好奇与欣喜。只有这样,佛教的发展才不至于因循守旧,乃至于孤芳自赏,才能以理智的眼光观待现实的缘起,从而顺利地与社会民众接轨,充分发挥道德教化与思想境界提升的功用。如明朝憨山大师说:“菩萨全以利生为事,若不透过世间种种法,则不能投机(投合机缘)利生。”(《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四十六)
由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现代科学兼顾物质和精神而特别侧重物质世界,佛教兼顾精神和物质而侧重精神世界。虽然研究领域各有侧重,但都是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彼此之间能取长补短,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现代科学在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而佛教在认识和改造精神世界方面则有一套完备的方法,如果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促进人类社会获得真正的科学发展,从而稳步获得持久的物质享用和深广的精神幸福。因此,现代科学与佛教联盟,有可能会是时代的一个趋势。